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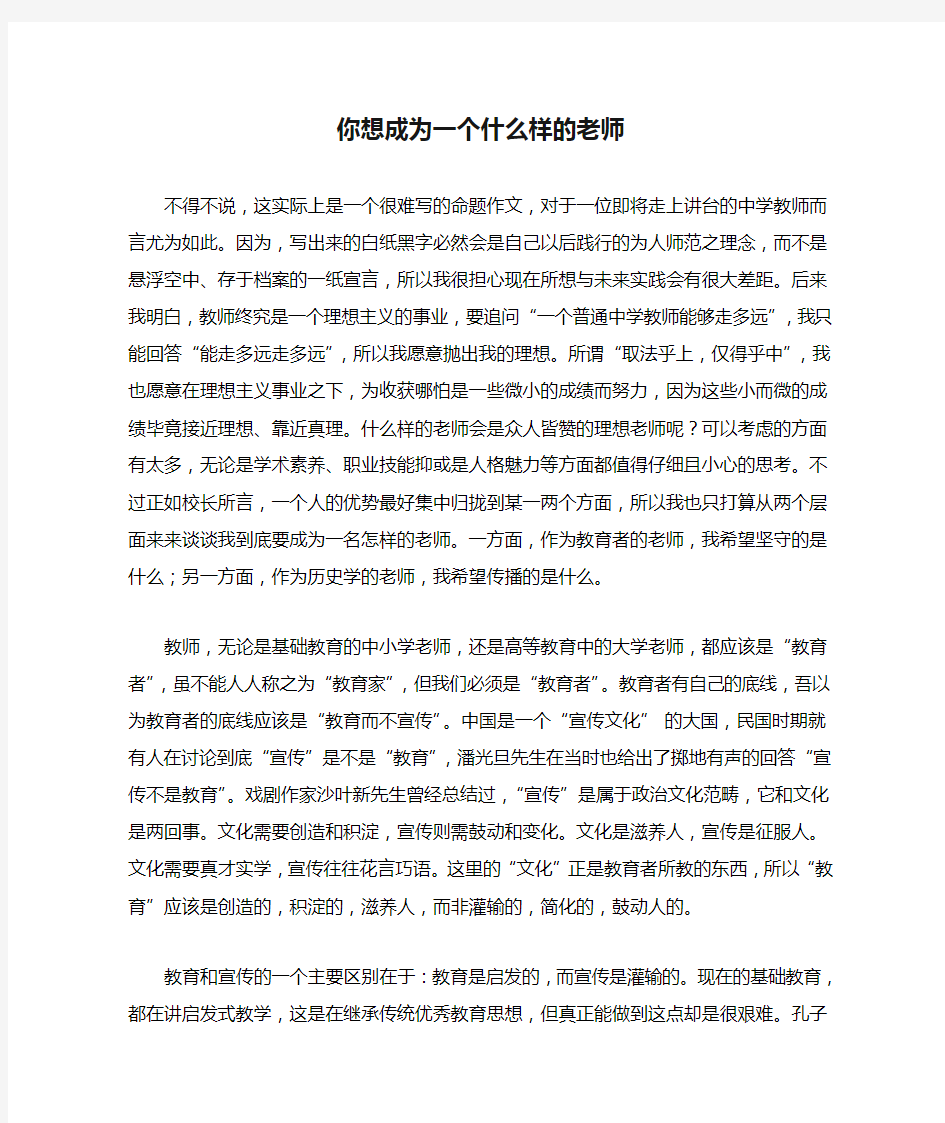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不得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写的命题作文,对于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中学教师而言尤为如此。因为,写出来的白纸黑字必然会是自己以后践行的为人师范之理念,而不是悬浮空中、存于档案的一纸宣言,所以我很担心现在所想与未来实践会有很大差距。后来我明白,教师终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要追问“一个普通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我只能回答“能走多远走多远”,所以我愿意抛出我的理想。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也愿意在理想主义事业之下,为收获哪怕是一些微小的成绩而努力,因为这些小而微的成绩毕竟接近理想、靠近真理。什么样的老师会是众人皆赞的理想老师呢?可以考虑的方面有太多,无论是学术素养、职业技能抑或是人格魅力等方面都值得仔细且小心的思考。不过正如校长所言,一个人的优势最好集中归拢到某一两个方面,所以我也只打算从两个层面来来谈谈我到底要成为一名怎样的老师。一方面,作为教育者的老师,我希望坚守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学的老师,我希望传播的是什么。
教师,无论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老师,还是高等教育中的大学老师,都应该是“教育者”,虽不能人人称之为“教育家”,但我们必须是“教育者”。教育者有自己的底线,吾以为教育者的底线应该是“教育而不宣传”。中国是一个“宣传文化”的大国,民国时期就有人在讨论到底“宣传”是不是“教育”,潘光旦先生在当时也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宣传不是教育”。戏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曾经总结过,“宣传”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它和文化是两回事。文化需要创造和积淀,宣传则需鼓动和变化。文化是滋养人,宣传是征服人。文化需要真才实学,宣传往往花言巧语。这里的“文化”正是教育者所教的东西,所以“教育”应该是创造的,积淀的,滋养人,而非灌输的,简化的,鼓动人的。
教育和宣传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教育是启发的,而宣传是灌输的。现在的基础教育,都在讲启发式教学,这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教育思想,但真正能做到这点却是很艰难。孔子就是启发式教学的鼻祖,颜渊说夫子是“循循然善诱人”,孔子也自认“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其得意的教育方法,所以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不是宣传家。潘光旦说:“教育不预备替人应付环境,解决问题,而是要使每个人,因了它的帮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想法应付,想法解决”,而宣传者则“假定智慧是一部分人的专利的东西,只有这一部分人,比较很少数的人,才会有成熟的思想,才能著书立说,才有本领创造一派足以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其余大多数的人只配听取,只配接受,只配顺从”。可以看出,教育的启发会是创造的,会是独立与自由的,而宣传的灌输经常会是口号式的,甚至会是欺骗的,也是依赖与顺从的,这在中学的文史哲教育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比如历史课,面对简化的历史,怎样做到“历史教育”而非“历史宣传”?这么说并非意味着教材就是“宣传”的材料,因为教材毕竟不是什么花言巧语,我们承认教材中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只是教材中的“历史”过于简化,也过于选择性。因此多数人会认为教材是“宣传式的材料”,因“宣传”而变得对教材产生疑问和不信任,如此,对教材和教材中的历史都不信任,我们怎会希冀中学课堂成为一个信任缺失社会中对抗丑恶的最后堡垒?作为基层的历史老师,我们不指望整个教育体制会突然满足自己的愿望,比如把原有教材内容推倒重来,我们能做的是点滴的改良,比如善于“利用教材”,而不是直接“教教材”。我们可
以尝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补充历史的另一面,比如课本不重视“人”,我们就要重新发现“人”。以“洋务运动”为例,课本中洋务运动一节中提到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都是晚清最知名的士大夫代表,我们课本只是把他们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一笔带过,似乎他们只是一场经济运动中的经济人,其实他们代表的可以是整个晚清社会,他们丰富的生命历程恰恰是历史学最富有人性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在介绍洋务运动时稍微花些时间来讲讲这些晚清的士大夫。至于时间的把握、课标知识的讲授等技术环节,我想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关键取决于一位老师用什么理路来把这些知识点串起来。各种校本课程的开设自然也是丰富“历史教育”、对抗“历史宣传”的佳途之一,但重要性不比国家课程,因为国家课程的教授占据了教学的主体,因此善于利用教材的老师我是很佩服的。不过,各种校本课程依然非常重要,例如“国别史”的教育就很重要,拿俄国史为例,俄罗斯一千多年的文明是否只是教材中的所讲的“不完全的前苏联史”或者“中苏关系史”?显然不是,这是明显的“宣传”,而不是“教育”。就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素养而言,不了解俄罗斯的传统历史文化也会很难认识为什么苏联会成为苏联,而不是成为另一个西欧民主国家,中国史亦然。
无论是“钱学森之问”还是“温总理之忧”,对“大师”的追寻依然是国人的心病,这表现在对诸如诺贝尔奖的各种遗憾之上,我们也为此责问当下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者。最近文化界的一件事似乎让我看到“钱学森之问”的可能答案之一,那就是建筑师王澍的“横空出世”。王澍因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获得全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借此反思当下的教育理念。建筑学长期被当成技艺之学,在建国后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多被划入理工科学校。从今天城市中冷冰冰丑陋的建筑中就可以看出,我们培养出来的建筑师多是没有人文情怀的工匠,也没有历史文化的熏陶,但是王澍代表的确是另一种可能。王澍说他首先是一个文人,然后才是一位建筑师。他爱中国古典诗词书画,他爱翻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他会按照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行走,去寻找书中提及的村落,他过着诗意般的人生,因此他也就有了一般建筑师没有的人文关怀。所以,他设计的商业住宅会意图恢复传统邻里的互动与交流,以对抗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人带来的冷漠与孤独;他设计的校园会体现传统文化对诗意的追求,以对抗充斥社会的庸俗且毫无美感的商业建筑。正因为此,王澍被世人认可,获得建筑界的最高奖,我们也可见一位年轻建筑大师的形成。
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都是“职业教育压倒博雅教育”,学术以分科为贵,技术以专精为高,但从王澍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教育的弊端。这种偏重专门技术人才的教育,在潘光旦看来实际上也对“宣传”起着“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功用。在他看来,专门教育固属重要,但专门教育必须建筑在良好的普通教育之上,才不至于发生流弊。一个人固然可以在专门领域做出贡献,但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一旦出了专门领域,也就给各种“宣传家”以机会,最终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精神也就会逐渐丧失,成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庞勒所谓的“乌合之众”。如今的大学多少进行了反思,各种博雅学院和跨学科的研究院应声而起,这实际是对传统通识教育的回归。但对于中学和中学老师而言,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要给高校输送具备学术素养的学生,这种学术素养必然是具备“通识”视野的,而不能仅是专门技艺的,人文学科自不待言,理工科的学生也应如此,王澍的例子就告诉我们人文素养的重要性。对于大学生而言,这种素养可以自学,
但对于中学生,中学老师的人文视野则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学生的“向师性”使然,所以我理想中的老师必然具备这种素养。
如此,学校的一些通识课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学生都如王澍一般自觉地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我们要创造人文的环境,这就是人文通识课的重要性。这当然不是某一个老师可以完成的任务,可以学科之间合作,这也是学术专门化之后不得已的办法。比如最近听说学校要开展关于“水与文明”的扩展课就很有意思,化学中的“水”文明,文学中的“水”文明,历史学中的“水”文明,地理学中的“水”文明,政治学中的“水”文明,如能开展必然很有意义。具体到某一具体学科,这种教育如何可能呢?当然,通识教育不必然是跨学科的,英文中的liberal education也经常被翻译成“通识教育”,这种教育贵在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熏陶,所以作为一名历史学老师,这种人文教育不仅可能,而且不必和专业矛盾。比如给学生介绍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如梁启超、吕思勉、钱穆、顾颉刚、陈寅恪、蒋廷黻、郭沫若、翦伯赞等人,介绍历史学家必然会涉及他们的史学思想以及他们所处的变迁社会,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人文的浸染和熏陶也必然是从这些人物中获得。
除了坚守“教育而不宣传”的底线,作为一名历史学老师,怎样让自己成为“历史”的代表,或者说怎样让“历史课”真正成为“历史课”,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介绍历史学家当然能突出历史学的特质,因为这会涉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是一个学科的内在发展脉络,学生对此有了解也必然会增强历史学的特殊性,而不是追问“历史学到底是干嘛的”。傅斯年曾说历史课应增进对“人类”和“人性”的了解,把史学当“人学”,这确实应该成为历史学的特质。已逝的史学家自然也是历史中的“人”,但更多的“人”还是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史家罗志田先生曾说过:“中国向有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纪传体”传统,后被梁启超攻击为无数墓志铭‘乱堆错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学仿效的是西来的章节体论著,略近于以前正统士人不屑为的章回小说。随着西方社会生活中人的一步步异化和物化,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股很强的潮流,即人的隐去。而西方史学恰是我们想要摹仿的榜样,结果是我们自身的史学论著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类别、角色、数据、甚或指数,而越来越少见具体单个的人”。今天的历史教材除去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显得有中国特色外,其实也一方面与国际“接轨”,也即隐去了“人”,这多少使史学的“教育”功能缺失,因为人性的光辉往往需要具体的人来师范和警醒。历史老师怎样做到这一点,恐怕只能尽量做到诚实,真实展现这个世界的丑恶和美好。
写了这么多,显得芜杂,但都是在前辈学人对教育与历史教学思考之下的一点自得。我知道,要能实现这些理想几乎有些不可能,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